 |
|
人算什么 ――儒家与基督教之人性论比较2016-07-22
杨联涛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孟子·告子上》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圣经·创世纪》1:27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圣经·罗马书》3:23 引言 “人算什么!”几千年前,诗人大卫面对“人”发出如此的概叹。身为人,却对自身不尽然了解,因此,人常常将“人”作为研究和描述的对象。 人算什么,一方面有着无上的尊贵荣耀,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另一方面,不过是出于尘土,一声叹息之后,所有筹谋都将如飞而去,复归尘土。 人算什么,再没有比人更为矛盾的个体:一方面,圣洁如天使,另一方面,败坏如恶魔,两者都在人类活动中不断表现出来。因此,就有各种文化、宗教、哲学对人性的各种界定:有说“人性本善”,有说“人性本恶”。同属中国儒家思想的早期几位重要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人性也得出了似乎截然相反的界定: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但更多的汉语学者对儒家人性论的总结是:人性本善(下文将详述之)。 而基督教圣经对人的描述似乎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创世纪开篇便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形像所造、不同于其他万物的受造者。如果这位上帝是全善全能圣洁的上帝,那按上帝形像所造的人必然拥有来自上帝形像的圣善与尊荣;另一方面,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17:9),保罗也引经据典地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3:10-12)加上受奥古斯丁以来的原罪论影响,基督教神学对“人”的认识从此就烙上了一个无法否认的印记:罪。 如此看来,对人性的认识,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相对立与矛盾就势所难免了,儒家宣扬人性本善,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然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认识就真是这样互相对立不可调和吗?本文试图就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性论与基督教神学中的人论作一简单探讨,并试图从中寻求两者间在“人性”这一问题上会通,从而达成儒家与基督教在相关问题上的对话与融通,让基督真理在中国文化的厚土中弘扬光大。使更多的中国人,无论是信仰,还是不信仰基督的中国人,在两种文化与信仰的立场上能彼此接纳、彼此尊重,彼此补充。 中国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虽源自于两个不同的民族,但并非绝然对立,那位几千年来将自己的智慧与知识启示予希伯来民族先祖们的上帝,同样也启示着华夏民族的先贤们。虽然两个民族对启示的回应是如此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上帝在其中的工作。因此,笔者将从“普遍启示”的角度来看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性和基督教神学中的人论。这也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话的基础。 作为一个基督徒,笔者会首先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处境中)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深感上帝对华夏民族的厚爱,先贤们留下的深遂思想、道德典范、社会、政治及人生理想信念值得今天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我们仔细思量。之所以说首先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来谈论这一话题,并非贵“西”(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化)轻“中”(中国文化),只是因为笔者若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便不会对基督教的人论有所了解或接触,也就不会产生要对中国儒家的人性论与基督教神学中的人论进行对比的念头了,因此,本文仅仅是一位生长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基督徒对两者间关于人性论这一话题的粗浅思考,若能抛砖引玉,此愿足矣。 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演变、发展与完善,本文不打算罗列中国历史中人性论的演变及各家观点,而是仅仅集中讨论早期儒家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论观点。在讨论基督教人论时,也会更多的集中于圣经本身的启示上。 一、儒家的人性论 (一)、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性观 孔子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他以仁为核心,论及义、礼、信、孝、直、忠、勇等,而这些对“仁”的讨论又源自他对生活的体验,也成为他的人生追求理想和教导弟子为人处事的准则。 “仁”是什么?孔子对“仁”似乎没有明确、一定的定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指的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篇》) 而当“樊迟问‘仁’于孔子时,孔子的回答则是:“爱人。”(《论语·颜渊篇》) 孔子的另一弟子颜渊问‘仁’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篇》)不同的人问孔子关于“仁”的道理,孔子给出的答案似乎都不同,但总而言之,在孔子看来“仁”就是对人之善的定义 ,而善的表达则是在与人相处中体现。 “仁”从哪里来?在孔子看来,“仁”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它离人不远,“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论语·述而篇》)由此可知,孔子的“仁”是发乎内心的悲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伦及道德修养的基础。换句话说,“仁”是发乎内在的人之天性,是孔子对人性的认识。他不谈“性”,只论“仁”。这内存于人里面的仁,就是他对人性之善的定义,正是人有“仁”之善性,人的自我修养以达“仁”之道德最高境界才成为可能。 对孔子来说这种来自内在的“仁”,是人与人间的互动,二人为“仁”,人在与人相处中发扬内在的仁,亲亲而后及众,由己而达人,以至由此知“天”。孔子对“仁”的理想,就具体的体现在他与自然(天命)或他人之间的关系上,甚至应用于政治上。他的“仁”人君子的理想人格观念,成为了儒家甚至东方人的生活方式。 在《论语》中,孔子对“仁”谈论更多的、也是“仁”最根本与实际的体现,则是他的“孝”,“仁”首先在家庭人伦的关系上得以表达,这就是儒家的“推及及人”之道。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 对父母的孝,不只是停留在养,更是尊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篇》),在孔子看来,孝敬父母,以父母之事,为人生第一要事,父母若健在,人就当留在父母身边尽孝,而不要离家到远方去:“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篇》) 父母健在时尽孝,父母去世后,仍然以一定时间的守丧、遵守父母之教训来表达对父母的孝与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父母亡,“三年仍不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论语·述而篇》)。孔子特别强调人之“仁”在家庭中的表达。因为孝乃“仁”之本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 在《圣经》中,孝敬父母作为一项命令明文列入“十诫”(出20:12)。十条诫命可分为两部分,前四条是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后六条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而排在后六条之首的便是孝敬父母。儒家的“仁”虽然少有论及人对“天”或“上帝”的态度,但强调在人伦关系中,发扬人性之善,以不负天命。人性善的开始,乃从孝敬父母,亲爱家人开始,推及己及人,与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互相回响,有异曲同工之妙。 爱是孔子“仁”的核心内涵:仁者,爱人。这爱在孔子那里,是从家庭开始,从身边可以触及到的人开始,在爱中达到人之善的最高境界。这爱,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上帝是爱,保罗也强调:“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人能爱,是因为上帝是爱,并且首先爱了人,爱从上帝而来,人回应上帝的爱的最好方式就是爱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呢?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约壹4:20-21) 无可否认,孔子的“仁”学体系,对中国儒家思想乃至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子以“仁”道出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爱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子不仁”、“诸侯不仁”、“卿大夫不仁”(《孟子·离娄上》)的时代,处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孔子,对人性仍持乐观的态度,一再以“仁”、“爱”作为人生理想的追求,并穷其一生周游列国,不遗余力地宣扬、推行其“仁”之理想,更用尽一生心力教导弟子,遵循“仁”道。在孔子“仁”之理想里,人自身是和谐的,君臣、父子、人人间都是和谐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孔子所讲的“仁”道。之所以难以做到,非内容之高深莫测,难于实践,而实在是他所忽略或不愿意面对的人性中的“恶”,正是因人性有“恶”,使他的“仁”包括“仁政”理想无法实现之因。正如赖德烈在论到华人文化及宗教的特点是所说的那样:“孔子和其他的华人学者强调,伦理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人的举止会决定他在来世的命运。所以,伦理规律也并不缺乏强硬的制裁和惩罚,但它缺少另一个积极的动机,就是对上帝的责任感和对上帝的爱慕。” (二)、孟子的性善论 与孔子不直接谈论“性”或“人性”不同,“性”或“人性”是孟子的一个重要话题,孟子在与告子关于“性”的辩论中,提出了他对“人性”的观点,首先,孟子对告子的“生之谓性”,人性无所谓善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提出了人性善。孟子认为人的这种善性生而有之。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也人;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皆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又如:“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如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 又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 上述言论显明孟子的人性观,他认为人性本善,这种善性是人为这人的根本,是生而有之的。 其次,他将人性与饮食男女等属动物的自然属性区别开来,认为色食之类不是人的本性,这些是人和禽兽共有的,不足以反映人的本质特征,他将他的人性论建立在其社会属性上,他看到人在社会活动及与他人的互动中表现出区别于动物的善性来。他与告子关于人性的对话说明这一点: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 其三,孟子的“性善”,并非一种静止的状态,或者以为人性本善,就无需作为,无所作为。相反,孟子强调,这种人皆有的善性,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 人必须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才能达成完全的性善。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目的不是单纯讨论人性究竟是善是恶,而是在善恶纷呈的社会现象中,以“人性本善”作为解决现象之恶的途径,孟子借着人性善,强调人必须“把握并顺从自己的本性之善,率性而动” 在这一前提下,孟子提出了“人皆可为尧”(《告子下》)的理论。正是这一理论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不懈追求,以成达人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尽心下》 孟子性善论,值得肯定的是,他将人性与动物性区别开来,肯定了人与动物之别,人之所以为人,不是生而有之的食色之性,而是存于天性的“善端”,这“善端”组成人对仁、义、礼、智、信等高于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人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只有动物欲望,便与动物无异。在《圣经》的记载中,人与动物同属受造物,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被称为高等动物,说明人与动物在生物学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圣经明确启示,虽然人与动物都是受造物,同被置于一个环境,都会受环境影响,都以环境为依托。但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上帝的形象,人在与上帝、与其他人、与动物界的关系中有一定的主动性,以确立人之与动物不同。孟子不谈创造,但从人性本善的特质中,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肯定人作为人的尊严与高贵。 在孟子强调人性本善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许多人弃掉人之为人之本性,单单追求属于动物的自然属性的可悲,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他所主张的通过自身修养将人本有的善性发扬出来,对促进人伦道德修养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顺从自己内在的善本性,率性而动,难免缺乏动力,特别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种反求诸己的内在修养方式实行起来颇有拦阻,毕竟社会现象中的“恶”实际存在,这“恶”无疑成为人性中“善”的试探与挑战。基督教则强调人可以在圣灵的帮助和引导下,向着上帝为人类所设定的“人”不断更新、“象天父完全一样”的旅程行进。 (三)、荀子的性恶论 在先秦时代,关于人性的观念,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便是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关于“性恶论”的论述主要记载在《性恶》篇中。荀子对人性有何定义呢?荀子认为天生的、未经过任何学习或雕琢的称之为性。他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篇》) “性者,天之就也。” (《荀子·正名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篇》) 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看到的是人性所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他把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罪恶现象归结为人的本性,他以“人性恶”为立论,列举了一系列人性丑陋的事例,最后得出“人性恶”之结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篇》),故荀子结论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 正因为人性是恶,要对付这恶,实现仁义道德,现实“礼”就显得必须。就如荀子关于“性恶”的结论那样,人性恶,虽有善的表现,但并不是天性使然,而是通过学习、追求而达到的(善者伪也)。在这一命题中,荀子肯定了人性之恶可以通过教化、修为而成其善。 荀子的性恶论,与其说是在论述抽象的“人性”,不如说是为儒家的仁义道德理论寻找一个可以施行的基础,人性恶,礼义废,道不行,并非人所想要的状况,人天生性恶并非人的定局,这一恶之天性也并非不可以改变,人可以通过学习与追求来改变,就象古代的圣人,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性本恶:“凡人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但他们被称为圣人是因为学习的结果:“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在荀子性恶论的潜台词则是否认“天命”,予以人生以努力追求之意义,尽管人生而性恶,但并非破罐破摔,也不能为自己的恶寻找借口,而是用一套伦理教化,使性恶之人性能以改变为善之人生“蓝图”置入人生的追求之中。将尧、舜作为教化之榜样立于性恶之人面前,肯定了人自身努力与选择的价值。《圣经》讲人是上帝创造,上帝对人拥有绝对的主宰权,但上帝并没有将人创造成一个没有感情,不用思考,不作选择,也不用负责的机器人,而是赐予自由意志,并明确责任与界限,人可作自由选择,尽管最初的人滥用了上帝赐的自由意志,破坏了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从此人便陷入罪中,但在罪中的人仍然不缺乏上帝在是非对错上的明确启示,仍然可在两者进行选择,最终承受自己选择的结果。人在选择与承担的过程中明确人之价值与意义,并认识自己。从这角度看荀子的性恶论,就明白人在恶(罪)的现象中仍然具有的独特性。 有人说荀子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消极否定,我看倒不必定如此,尽管荀子强调人性恶,但他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人可能通过礼仪教化改变性恶,成为性善。性恶论实际是儒家伦理道德说教理论的潜台词,正因为人性本恶,人就需要效法圣人,追求礼义,成就其善。笔者同意李庆对荀子性恶论的评价:“荀子的性恶论,表现出更多的对人类自身力量的信心,表现出对人类和客观世界联系的重视,表现出思辨中整体的逻辑性。” 这种对人自身的力量给予肯定,表达了后天的努力比先天的本性更为重要的思想,也铸就了中国人面对自身及环境的恶劣态势时不放弃、不绝望的承受之力,这也是儒家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 小结 综观先泰时期儒家思想的人性论,从孔子肯定人内在的“仁”,到孟子主张“性善”,再到荀子主张“性恶”。荀子与孔孟关于人性的观点,似乎互相对立。但这只是表象,仔细对照他们的相关内容,无疑会发现,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看到了人性中的善,也看到了人性中之恶。孔子、孔孟论性善,看到的是人之为人之与动物的不同,他们虽没有更多谈及性恶,不是对恶的现象视而不见,也不是自欺欺人地有意忽略恶存在的客观现实,正是因为他们看到现实中的恶,这现实的恶并不能掩盖人性本质中某种程度的善,并期望通过发扬人存在本质中的善性,以解决现实中的恶。荀子论性恶,从人类经验的角度,看到的是社会罪恶的普遍现象。但荀子也并非绝对地认为人之性恶,与动物无异。乃是透过对恶深刻的揭露,强调人必须接受教化,以改变人之恶的现实。所以他们都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人生修养的标准和方向,以追求仁、义、礼、智等为善,以不知礼仪,背仁弃义为恶。笔者同意李庆的观点,他认为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性善与性恶并非两种对立的观点,因为“他们对于人性的思考方式,对于存在着的社会现象,道德理念的认识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区别,不在于对同样的‘性’作出相反的判断,而在于对于‘性’,或人的本性内涵的规定和理解。” 并且,李庆认为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性善论”.,笔者很难同意将李庆将儒家思想对人性的认识归入性善论的观点,因为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并非纯善,也非纯恶,而是善恶共存。但无疑他认为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观点统一性使得历史上把孔子、孟子、荀子都称为儒家的原因所在。 孔子认识到人天生有“仁”,正是这“仁”成为道德萌芽的善端,人需要不断修身养性,让内在的“仁”充分发扬光大,并在朝向内在的“仁”的过程中重建被破坏了的礼乐秩序。孟子明确地将人之性与动物之本性区别开来,肯定了人之不同于动物者,乃生而有之的各种善端,正是这善端使人成为人,并成为人追求目标。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并不是指人的本质,乃是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他所列举的性恶例证,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罪恶现象。而最终,荀子强调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通过“礼、法”来改变人性恶,从而达到人性善。实际上,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从不同角度切入,但并无实质上的区别,都肯定了人性善,与人之恶共存的事实,只是各人的切入点不同而已。无可置疑的是,无论是孔孟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未离儒家德育教化的宗旨,强调人性之可塑性和自主性,否认天生圣哲或单一的非善即恶的人性定论。 孔子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属性上的性善论,肯定了人在彼此关系中的自我确认,正如基督教强调,人在关系中才能对自身有正确的认知。孟子强调人生而有之的性善论,与禽兽共有的饮食男女区别开来,肯定了人之与动物的区别,这一区别成为比其他动物高等一点的人当有的社会责任。同时,孟子也指出这种性善,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为人后天的努力留下了空间,是一种积极向前的人生观,否定将“人性本善”作为人生定论。从创造的角度看,上帝起初创造的人,是“甚好”,不知罪(恶)为何物,但人必须在人生的过程中,在与其他受造物相处的过程学习如何运用来自上帝形象的善,作正确的选择,以承担起作为人应有的责任。从救赎角度看,基督的救赎全然是上帝的作为,罪中失落的人,在基督里得以寻回,同时也强调人努力追求成圣的重要,上帝的救赎及“预定”并未代替人当有的回应与行动,正是在恩典的驱使下,人在不断努力向前,追求完善的进程中体会并活出上帝所赐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儒家与基督教在对人性的认识上都不是非善即恶的单一定论,都强调了人在向善或向恶中所有的自主性与所承担的责任。 在简单讨论了儒家人性论之后,下面让我们来简单地看看基督教对“人”的认识。 二、基督教的人论 《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人是按上帝形像所造,且是在上帝将万物都创造好之后才开始创造人的。在圣经对人的创造的记载中,无论是创造的过程,还是创造的材质,都与上帝创造其他万物不同。创世纪1章26至27节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在创世纪第2章的创造故事又如此记载:“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 基于圣经的启示,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便有了下列观点: (一)、人有上帝的形像――性之善 从创造故事中,告诉我们关于人的第一个信息是:人有上帝的形像。 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关于上帝的形像,有多种解释:“1、关系意义――人与上帝之间有独特的感通关系(relationship);2、代表意义――人与其它万物有不同的责任与使命(mandate);3、实质意义――道德判断,爱,群体关系,创造性,理性。” 关于上帝形像的解释不只上述一种,本文无意对“上帝形像”作过多神学上的探讨,也无意去分辨“形像”与“样式”之分别,因为无论对“上帝的形像”作何种解释,由上帝形像所定义的人无疑决定了人本善的受造本质。 上帝是那位绝对至善者,有上帝形像的人,无疑具备从上帝形像而来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人之尊贵,也决定了人本质上分享着来自上帝形像的某些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性本善,因此,上帝是纯善的。当然,人性本善是建立在上帝的善与神圣之上,而不是上帝之外的其他任何因由。因为善的上帝绝不会造出恶的人,恶并不在上帝创造的旨意中。 人本善,首先,从创造的角度说。人是按上帝的形像所造,人性是由“上帝形像”――至善的本源――而非人的经验,或现实中人的表现所定义。 其次,在创造故事中,圣经作者多次提到,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创1:10,1——18,21,25),而当上帝创造的极品之作――人――完成时,上帝则看为“甚好”(创1:31)。人是上帝创造的高潮与中心,被造之初人圣洁、神圣,与上帝亲密无间,可与上帝在园中自由往来,人也没有羞耻感(创2:25),更并不知罪为何物。后来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引诱,误用了创造之主所赐的自由意志,离弃了上帝的命令,犯罪远离了上帝。以致亚当夏娃之后的人都成了罪人,这就是神学上的原罪之说(既有原罪,岂不更有原恩?或原善?因为没有后者,就不存在前者)。即使人成了罪人,但上帝在历史中所施行的一系列拯救作为,都将人作为所有受造物中最钟爱、宝贵的对象,甚至宝贵到亲自道成肉身,从永恒到有限,自限尊荣与荣耀,甘愿受辱(上帝甘愿在三方面受辱:第一,他道成肉身,放弃神权,屈辱为人;第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罪人,忍受死的耻辱;第三,上帝降低自己,甘愿活在我们这种人所组成的教会里。)降世为人,拯救世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第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只启示了上帝对按他形像所造之人不离不弃的拯救与爱,同时也肯定了人的价值或人性之善面,神圣的道没有成为天使,而是成为有肉身的人。 因此,尽管基督教神学上有原罪说,尽管圣经不断的提到人的败坏与堕落,但圣经对人性并不是一刀切的善或恶,从创造本质来看,人性本善。正如江丕盛说到:“对人性的否定实质上是对创造他的上帝的攻讦与嘲笑。在基督教的人观中,人必须面对自己的真相与受造本相的天渊差距令人羞愧,甚至绝望。但受造本相却仍宣告创造主对人的不舍之爱,创造原意没有因人的堕陷而废弃。换言之,‘失乐园’仅是‘重返乐园’的序曲。事实上,‘全然堕落’的教义必须在一个‘全然恩典’的救赎语境中才可有全面而正确的诠释;前者必须基于后者,作为后者所衍生的真理。就基督教神学而言,‘人作为上帝的形像’绝不是自然神学或理性哲学的认识,而是来自福音的真知识。在恩典之外,人无法得知‘上帝的形像’更遑论建立‘上帝形像’的人观了。‘人作为上帝的形像’既是基于恩典的启示,这真知识的目的就不在于定罪,而在于赐盼望、平安与生命。这样看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3:23)并非基督教人观的焦点;‘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3:22),使他们‘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罗3:24)才是基督教人观的核心真理。” 诚如“法国神学家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说:‘人性就其本性而言是良善的。’” (二)、罪的侵入,“失乐园”――性之恶 人有上帝的形像,但人不是上帝,人不似上帝不会受影响,因为除了有上帝的形像的尊贵荣耀外,人同时也有尘土的一面,因为上帝用尘造人,然后在人的鼻孔里吹入生气,人才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所以,出于尘土之人必归于尘土,尘土成为构成人的要素之一。尘土也决定了人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当亚当、夏娃用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违背上帝的命令,便打破了人与上帝间的无间关系,罪便因此而产生。上帝创造人并赐予人自由意志,是让人自由的回应上帝,而人借用自由选择背离,从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被罪所奴。希伯来民族对罪最本质的定义指人背离上帝。因为对上帝的背离,人与其他受造间关系也被打破。在创世纪第1至2章的创造故事中,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6-27),人被置身于“与上帝”和“与他人”的两个关系之中;当上帝让人修理看守各样的受造物时,人又被置身于与自然的关系中(创1:26;2:15)。上帝将人创造成为是关系的、社会性的存在。而“罪”最严重的问题是将关系破坏,首先是将人与上帝间的关系破坏,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参创世纪1-3章)。诚如傅国朝所说:“罪的状况可视为对上帝创造的人类存在的结构的破坏。如果说我们被造时与全然有别于我们的上帝有关系,与相对有别于我们的他人有关系,那么,罪就是我们与全然的‘他者’的实质关系的否定。” 舒也从“神圣价值”角度解释“罪”,让人认识罪的本质及其严重性,不在于人做了什么,而在于对上帝最初造人的意图及上帝神圣价值的背离,他在“价值存在的二难:基督宗教视野中的人”一文中如此说到:“仅仅违背了上帝的话,就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可见这‘话’意味着上帝绝对的权力,并且,仅仅吃了一个果子就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孽,这也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被视为绝对的价值。这一行为被解释为‘原罪’,或许它可以从价值角度得到解释:这是对上帝之绝对价值的背离。” 没有比破坏了关系――上帝创造之时所定的神圣秩序――更为可怕的罪了!当秩序不在,关系不存时,人便无所敬畏,无所顾及,各种可怕的罪行便应运而起。这就是基督教对“罪”的本质叙述。人不听从上帝的命令,想要脱离创造之主而自为其主、自作主张,这就是罪了,这就是人的骄傲,也被众多圣经作者视为众恶之首。这罪不在于人是否做了某个社会所定义的法律所定不可行之事,或某类道德规范所谴责之事,而在于人背离了上帝绝对神圣的价值观。这种背离使上帝与人不再如创造之初自由往来。因此,人被赶出象征人与上帝和谐无间的伊甸园。人与上帝关系的破坏,又影响到了人与他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这就是基督教关于人的罪的核心观念。 人违背上帝命令,远离上帝,从而使人里面上帝的形像受到亏损,继而各种恶行便在人类历史中不断上演。尽管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不断进步,文明不断更新,但人之恶却并未因为社会的进步、科技有发达而有所改观,反而有愈演愈烈之态势。 自从人来到这个世界,便经验到现实中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恶,这与创造本身的善形成对立,而这两者都并存于圣经的叙事中,善恶并存,这是每个站立在上帝面前的人无法回避的事实:人的尊贵与卑污、神圣与罪恶,这便是基督教人论中的悖论。圣经“一方面肯定人的尊严与高贵(上帝形像的内蕴与延续),一方面也肯定人的失落与堕陷(上帝形像的亏损),从而可以理解人性之中善、恶并存的事实。” 正如儒家思想对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一样。性善与性恶是人生存现实,基督教与儒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现实,都有着如此相似的观点,这不能不说两者都有着从同一位上帝而来的启示。与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圣经不只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不只是将一套令人敬畏的伦理道德抛给我们,让我们去追求成为圣人,以达成自身的功德圆满。基督教从人性恶中看到一个事实:没有人可以靠自身的修行解决“人”的问题;同时,基督教也从人性善中赐予一个盼望:我们本是按上帝的形像所造。圣经的特别启示,让人认识到上帝为拯救如此不堪的人,愿意付任何代价,不只教导我们律法条规,更是赐予能力去完成人生的朝圣之旅。这是基督教人性观与儒家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它是既看到事实,赐下教导,更提供能力。它是一个双回路的人性观。因此,谈论基督教的人性论,就不能止于剖析人究竟是“善”或“恶”的既存事实,更是这一事实背后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这计划无疑应该是基督教人论的重要延伸。 (三)、因救赎回归――新造的人 在新约中,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上帝启示的顶峰,太初原有的“道”(Logos)进入世界,取了肉身,住在人中,将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显明(约1:1-17),将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显明,也将旧约基础上人堕落后的人论予以重新定义。 道成肉身本身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肯定了“肉身”的价值,至善的道(Logos)成为有限的肉身。另一方面,表明有罪的人并没有被抛到无望的深渊,上帝并没有因为人的败坏与堕落,任由人在罪中沉沦与灭亡,而是采取了拯救措施,并以道(Logos)成肉身的方式,向蒙昧无知的人启示了人(包含着肉身与受亏损的上帝形像的人)在上帝眼中的宝贵。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用钉死十字架、埋葬、复活的方式,为罪中的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上帝、与上帝和好的路,所要求于人的是用信心回应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所成就的一切,人便得称义,与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因此,保罗宣告说,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既说“新造”,是相对于“旧造”来说的,那就意味着上帝要借救赎使人恢复初造之时的形像。因此“道成肉身不仅是上帝救赎计划的转折点,也是圣经人论的新起点。” 是对人性的重新定义,被罪影响,亏缺了上帝荣耀的人,可以在基督里得以恢复,尤如再造,就象上帝起初创造人那样,罪被挪去,人与上帝的关系恢复。因为救赎解决了由罪带来的最本质的问题:关系。“救赎不仅是个人灵魂得救脱离这世界,而且是创造一种新颖而深刻的自由,能与上帝契合,与他人联合。” 尽管现实中在基督里的人从经验角度看,远远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但上帝不再以人有罪的本相看人,而是透过完美的基督看人;在基督里的人,也不再以各人的本相看己、看人,而是在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里面,用基督的眼看人、看自己、看世界,并将自己的人生主权交给创造、救赎之主。又蒙圣灵住在人里面,时常提醒、引导人“作成得救的工夫”(腓2:12)。 因着基督的救赎,圣灵将人从罪中释放了出来,使人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罗8:2),在基督的救赎中,人的尊严再一次在上帝的救赎之爱中突显出来(约3:16),这尊严是建立在人有“上帝的形像”这一创造的基础上,上帝的创造之爱与救赎之恩在人性的尊严中连接起来。 耶稣基督短暂的一生,活出了人性的尊严,不仅启示出真正的“人”的样式,也借此肯定了人的尊严。上帝“对人的尊严的最高肯定,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表达出来的;而他的复活,是人的尊严最终可以被体现出来的神圣基础。” 人要活出这尊严,就必须放下自义与骄傲,承认自己有罪,单单顺服上帝主权,不再像当初的亚当、夏娃,因想要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3:5),想要越过上帝的命令获得自主权、决定权,结果失去尊严,而在基督里的“新造”,有如初造时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与上帝间自由往来。 (四)、一切更新――“复乐园” 诚如王峙军所说:“没有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描述,圣经人论会是很不完全的。” 基督教人论不仅告诉人性的善与恶之事实,还为解决人类的问题预备了救赎,启示了救法,而这救赎不只解决人现在的关系问题,更解决人将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上帝为人类朝向完全设计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赐予了人类终极的盼望。正如人类的起源――创造――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人类的终极未来――“复乐园”――也是上帝神圣的旨意。创造之始与终极未来遥遥相对,创世纪与启示录遥相呼应,上帝起初的创造甚好,未来的新天新地无限美好,生命树的果子成为人与上帝关系永不被破坏的象征。这盼望成为基督徒的实际,也是基督教对罪人的期望,无论现实中的人多么“坏到极处”(耶17:9),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6:5),但至善的上帝将反转这一切,无论什么代价,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人心如何筹谋自己的事,甚至千方百计有意敌挡上帝,都不能改变或阻止上帝对人类的永恒计划,因为人是按上帝形像所造,造人的上帝绝不容许人与上帝不正常的关系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下去,他不只在历史中施行救赎,更将人及人类历史导向他自己的蓝图,就是上帝在永恒中的旨意(林前2:7;弗1:4-5;3:11),人将以全新的复活新样式与上帝面对面。而人类的结局,必然是一个更新了的新人,整个受造世界也会因人最后的更新而得着医治,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将真正、完全的归于和谐,正如先知以赛亚所盼望的那样: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以赛亚书11:6-9;参赛65:25 又如约翰所见的异象: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21:1-4 结论 从上帝普遍启示的角度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信仰,会使我们能放弃固有的成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真正的对话不是要以基督教文化取代儒家文化,也不是用儒家文化取代基督教文化,而是透过对话,互相尊重,相互理解,欣赏上帝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启示之美,更加存敬畏上帝的心对待儒家思想或其他文化,并作认真省思,以广博的胸怀,认识并接纳基督教之外的真、善、美,因为上帝是宇宙的上帝。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基督真理是唯一的、绝对的,正如耶稣宣告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14:6),除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徒4:12)。但作为一种文化,彼此间应该是互相尊重,相互学习的。约翰用来自希腊观念的“Logos”来解释希伯来信仰中的“WORD”,使本来不相关的两者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相遇:道(Logos)成了肉身。保罗传福音到罗马帝国各处,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及罗马文化相遇,他就用希腊人所能理解的观念阐释犹太的信仰,最终使犹太人的上帝也成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本来就不只独属于哪个民族的。不同文化间的相遇必然会有碰撞、会有争辩,这才成就了早期教会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处境中,用哲学观念与逻辑思维对基督教教义作了激烈、深入、精深的讨论,为注重“信心”的希伯来传统注入了新元素,最终确立了基督教根本的教义。我们既然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启示者与掌管者,每一种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或多或少的反映着上帝的启示,“文化成为上帝启示的舞台” 没有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认真的省思与体认,也无从对基督教信仰有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中国文化人性论与基督教的人论的比较与对话中,无疑让我们明白上帝在各民族的历史中所成就的美好启示,启发我们至少在以下两点上的思考: 首先,存开放的态度对待“人”。 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基督教文化,都主张人有性善一面,也有性恶一面,当然,人并不是善恶混合或半善半恶的怪胎,善恶并存于人性之中,这是人该清楚认识的一点,李庆在分析了孟子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后,得出结论认为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主张“人性本善”。笔者对此观念稍有不同理解,前文已经有所陈述,在此愿再次强调:从表面上看,儒家似乎是讲纯善论,但实际上,儒家并未否定人性恶之一面,也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性恶,就如孔子、孟子所面临的是“礼崩乐坏”的现实社会,他们都希望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中找到一条走出困境的途径, 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性善论。关于儒家各派对人性论的结论,本人更倾向于何光沪的观点,他在“欲之无穷与良知”一文中如此说:“尽管历代有众多的学者主张孟子的性善说,也有学者主张荀子的性恶说,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荀的‘性’字所指者各不相同,所以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现象,二人的学说是互补互足的。从总体来看,儒家既不主张纯善论,又不主张纯恶,这与世界各大宗教的主张是相当一致的。以基督教为例,基督教在本体论(不是道德论)上主张人是‘善’的(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且人还赋有上帝的形像),但是人又因堕落而有原罪。” 人的创造本质之善,是上帝要施行拯救的原因,因为上帝的创造旨意里不存在恶,他不希望创造之善在人的存在中永远被罪所蒙蔽,而人的现实之恶,则是上帝,也唯有上帝才能解决的问题。 存开放的态度看待“人”,就是以客观的态度认识自己,认识人之尊严,维护人之尊严,不做任何伤害人之尊严的事,让人活得更象人。同时,人当认识自己不过如尘土,是充满各种欲望,满了各种败坏的罪(恶)人,当放下自我的骄傲(因为罪与恶本质上始于人的骄傲),寻求回复人性中原初的“善”。 存开放的态度看“人”,实际也同样适应于对不同文化,就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而言,两者对“人”的认识进路不同,但都看到了人的问题所在,都对人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剖析,也都给出了不同的解决问题之方法。并且强调人之为人就是勇于面对和解决“人”的问题,人的意义也就在于在解决罪与恶的过程朝向人性中的善。除了对人性的认识如此相似外,儒家和基督教在人生价值上有着许多的共同性,都以敬畏、道义、友爱、尊重、秩序为善,以与之相反的为恶,中国的先贤们的思想多有智慧之光闪现,如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取利”思想;“孔子的仁爱忠恕之道;孟子的所强调的大丈夫的独立人格、道德的自律与自觉等。” 这些智慧之光、人生价值观,不亚于圣经的教导,我们很难将这些智慧及仍然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置于上帝的启示之外。 其次,存敬畏的心对待“他者”。 对“他者”的尊重是上帝创造的旨意,人是创造的杰作,人被上帝委派为其他受造物的管理者,而不是主宰者。人更不是其他人的主,可以任意对待其他与自己一样来自上帝形像的生命。对“他者”的尊严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人性”上。 人“有上帝的形像”,每个人都有作为人之善端,人当自重,更当尊重他者。孟子的性善论是他对生存的关注,顺从本性,率性而动,似乎只与个人的修养有关,但实际涉及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在《论语》中,孔子将“仁”的人生理想置身于人伦关系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基督教则更不用说了,上帝创造之时,将人置于关系中,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应的则有著名“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太7:12)上帝的创造不但决定人性,也决定人的关系: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在上帝的创造旨意中,孤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人只有在群体中才显其独特性,其身份与使命才得以确认(创2:18-20)。单个的人是违背上帝创造的目的的: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又将人安置在伊甸园,命令人修理看守。人在与他者的相处中,才能体味并活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来。 而在人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上帝间的关系,没有对“绝对他者”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他者”的敬畏。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却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敬畏之心,儒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强调一个事实,若无对“天”所赋予的善性、对圣人的敬仰,但无法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基督救赎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与上帝间疏离的状态,他用生命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人与上帝和好(弗2:14-16),“两下”和好首先是人与上帝,其次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弗2:17-18)。 对“他者”的敬畏不只是一个信仰者的态度,也是人之为人的态度。敬畏使人深远,也使人广博,有敬畏之心的人,就不会以“己”为标准去评判“他者”,也不会想要以无可质疑的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是从尊重到理解,到肯定,到吸纳,这样对话才能形成。 人算什么?是人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不独属于哪个文化或宗教的问题,它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正因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的寻索与回答,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有许多共同之处,诚如林慈信在《比较人论――基督教人论与中国人性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基督教与中国思想能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找到共同点,或说交汇点。” 这个交汇点就是宇宙的上帝的普遍启示,有了这一交汇点,两个文化间才可能进行更多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使中国基督徒对自身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信心,更多的担当,同时也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清楚的确认,对中国社会有更多的责任,对福音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根有更多的使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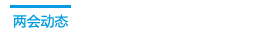  |
| 浙江光盐爱心基金会 | 中国基督教网站 | 金陵协和神学院 | 国家宗教事务局 | 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华东神学院 | 广东协和神学院 | 重庆市基督教两会 | 湖南省基督教两会 | 广西基督教两会 | 陕西省基督教两会 | 河南省基督教两会 | 北京市基督教两会 | 广东省基督教两会 | 湖北省基督教两会 | 四川省基督教两会 | 内蒙古基督教两会 | 青岛基督教两会 | 成都市基督教两会 |
|
版权所有: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浙ICP备15043450号-1 管理后台 |